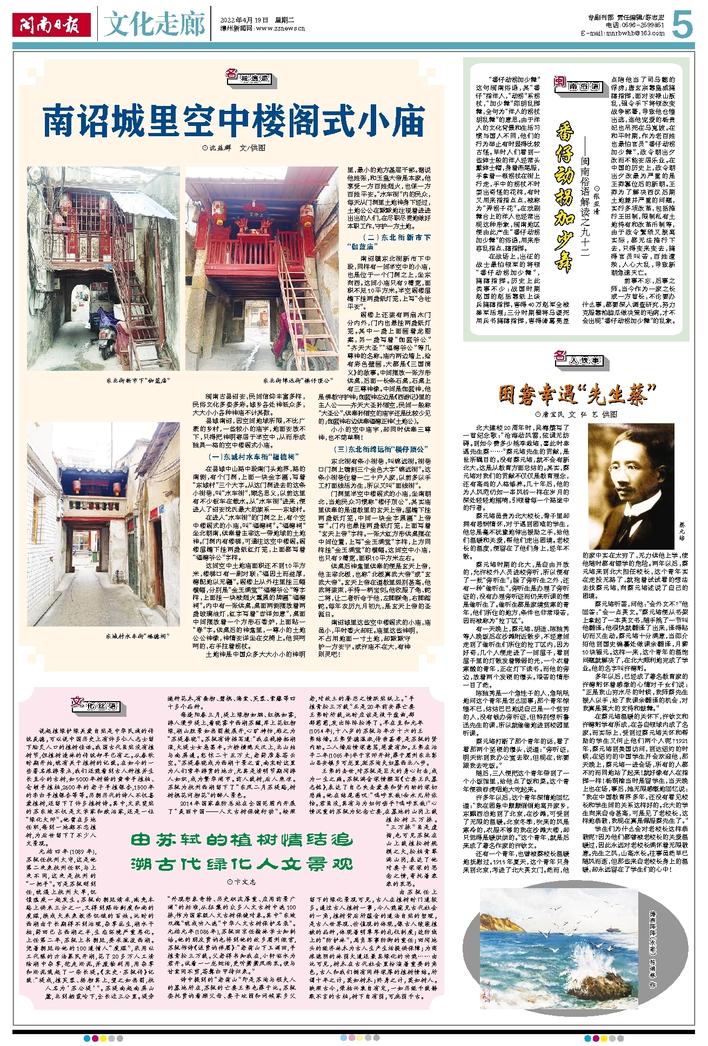说起植绿护绿关爱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留下脍炙人口的植树佳话。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植树节,但植树造林的传统却早已有之。从春秋时期开始,就有关于植树的记载。在如今的一些著名旅游景点,我们还能看到古人种植并生长至今的古树,如5000年树龄的黄帝手植柏、仓颉手植柏,2600年的老子手植银杏,1300年的李白手植银杏等等。历朝历代的诗人不仅喜爱植树,还留下了许多植树诗。其中,文采斐然的苏东坡不仅是文学家和政治家,还是一位“绿化大师”。他曾在多地任职,每到一地都不忘植树,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人文景观。
元祐四年(1089年),苏轼任杭州太守,这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任职,与上次不同,这次是杭州的“一把手”。可是苏轼刚到任,就遇上杭州大旱,饥馑瘟疫一起发生。苏轼向朝廷请求,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,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,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。此时的西湖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理,杂草丛生,湖水干枯,葑田已占西湖之半,生态环境严重恶化。上任第二年,苏轼上书朝廷,要求疏浚西湖。凭着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“度牒”,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,花了20多万人工清除湖中杂草,挖走淤泥,并废物利用,用杂草和淤泥筑起了一条长堤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记载:“堤成,植芙蓉、杨柳其上,望之如画图,杭人名为‘苏公堤’”。苏堤南起南屏山麓,北到栖霞岭下,全长近三公里。堤旁遍种花木,有垂柳、碧桃、海棠、芙蓉、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。
每逢阳春三月,堤上绿柳如烟、红桃如雾,游人漫步堤上,看晓雾中西湖苏醒,岸上花红柳绿,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,心旷神怡,称之为“苏堤春晓”。苏轼有诗描写道:“我在钱塘拓湖渌,大堤士女急昌丰。六桥横绝天汉上,北山始与南屏通。忽惊二十五万丈,老葑席卷苍云空。”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,南宋时这里为人们常年游赏的地方,尤其是清明节期间游人如织,成为繁华闹市。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。苏轼为杭州西湖留下了“东风二月苏堤路,树树桃花问柳花”的醉人景色。
2014年国家森防总站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“美丽中国——人文古树保健行动”。按照“外观形象奇特、历史积淀厚重、应用前景广阔”的标准,从征集的众多人文古树中选100株,作为国家级人文古树保健对象。其中“东坡双槐”就成功入选“中华人文古树保护名录”。元祐元年(1086年),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。他的朋友贾讷也将到他的故乡眉州做官,苏轼作诗《送贾讷倅眉》:“老翁山下玉渊回,手植青松三万栽。父老得书知我在,小轩临水为君开。试看一一龙蛇活,更听萧萧风雨哀。便与甘棠同不剪,苍髯白甲待归来。”
诗中提到的“老翁山”即是苏洵与程夫人的墓地所在,苏轼的亡妻王弗也葬于此。苏轼委托贾讷看顾父母、妻子坟园和问候家乡父老,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。“手植青松三万栽”正是20年前安葬亡妻王弗时所栽,此时应该是枝干盘曲,郁郁葱葱,发出阵阵松涛了。早在至和元年(1054年),十八岁的苏轼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。王弗贤德温淑,侍亲甚孝,是苏轼的贤内助。二人婚后情深意笃,恩爱有加。王弗在治平二年(1065年)卒于京师开封,葬于眉州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,距苏洵夫妇墓西北八步。
王弗的去世,对苏轼是巨大的身心打击,成为一生之痛。苏轼满含深情撰写《亡妻王氏墓志铭》,表达了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。他在结尾感叹:“呜呼哀哉!余永无所依怙。君虽没,其有与为妇何伤乎?呜呼哀哉!”心情沉重的苏轼为纪念亡妻,在墓地的山岗上栽植松树三万株。“三万株”虽是虚指,也可见苏轼在山上栽植松树规模之大,松柏青翠满山岗,表达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之情,寄托着浓浓的哀思。
由苏轼任上留下的绿化景观可见,古人在植树时门道较多。通过古人植树一事,今人能窥见古代社会的一角,植树背后所蕴含的道法自然的哲理,是古人世界观、价值观的体现。像古人陵寝植被的品种,体现着明尊卑的礼仪制度;边防线上的“防护林”,肩负军事防御的重任;田间地头的经济林木为古人生产生活提供保障;为商旅遮阴的林荫大道还兼具绿化的功能……由此可见,树木在古代社会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古人和我们拥有同样深厚的植树情结。所谓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;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。映照古今,荣枯兴衰自有定,一如历经千载静默不言的古柏,树下自有荫,可庇荫千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