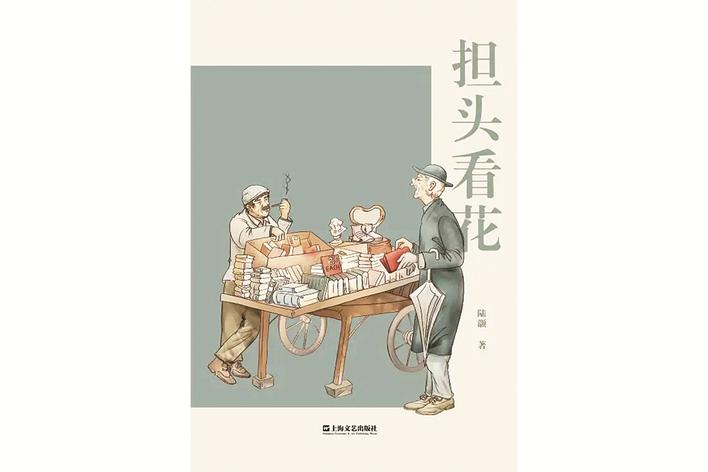▱曾丽琴 文/供图
几年前读到陆灏的文字,便惊为天人,更自惭读了几十年的书,竟是那么迟才识得陆灏。于是便检视自己,何以没有早发现之?检视之后便释然,陆灏混的不是文学圈,而是出版圈、藏书圈,这就难怪我等学文学又受文学所限之人了。
如何定义陆灏文章的文体?随笔?小品文?读书札记?都对的,但是这样的定义又有什么意义呢?关键是文章要写得好看。陆灏的书我是从《不愧三餐》买起的,然后回追《听水读钞》,等了四五年,终于又等到了这本《担头看花》。
《担头看花》与《不愧三餐》《听水读钞》取材上没什么不同,都是写中外那些老学者、老读书人、老作家甚至于老艺术家的作品、生活、行止、言语等。唯其不同的是,这本书中文章的篇幅比前两本书明显长了很多。之前两本书每篇均在800字上下,《担头看花》一书短的也要2000多字上下,最长的一篇《以赛亚·伯林的初恋》竟有万字。有趣的是,连“后记”也都写得比以往长得多。私下以为,这是因为陆灏读书写字到了一定程度,可以把许多胸中的东西串连起来,文章便恣肆了。就如他喜欢的钱钟书。
陆灏显然是十分佩服钱钟书的,三本书的开篇之文都是关于钱钟书的。但《担头看花》一书更为特别,书中竟有近三分之一的篇章与钱钟书有关。最主要的原因是钱钟书的《容安馆札记》是他近几年读得最多的书,所以,《担头看花》一书的前七篇便是“读《容安馆札记》札记”了。然而,若是用这样的篇名便没了情趣,所以,陆灏写的是《“吾家苗介立”》《“那么我就是众猫之王了!”》《出恭看书》等。
钱钟书博学强记,中西兼擅,他的散文《人·兽·鬼》已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,《管锥篇》就是一般的学者亦不敢轻易说读得懂,《容安馆札记》似乎还要比《管锥篇》高一个段数。该书出版的是影印本,内容的高深加上钱钟书那潦草的中英文笔迹,有如天书。有趣的是陆灏在“后记”中老实交代,他之所以能够写下这些札记的札记,是因为看了新浪博客上一位叫“视昔犹今”的整理稿。
年轻的时候读过余光中论散文密度的文章,深以为然。然而余光中论散文的密度也仅是说不要写太多大白话,把文章拖垮了。现在读了陆灏的这部《担头看花》,突然对余光中的“密度论”有了新的理解,虽然余光中写不出陆灏这种密度的文章。
就像《“吾家苗介立”》,陆灏从钱钟书《槐聚诗存》的一首写到猫的诗写起,写到杨绛回忆钱钟书的文章,写到广为人知的钱钟书帮自家猫与林徽因家猫打架的故事,才引出《容安馆札记》中对猫的多次叙述与考辨,后面还写到冒孝鲁的文章、吴学昭的记录、《管锥篇》对猫名“苗介立”的钩沉、苗介立的失踪等,最后收在钱钟书“余记儿猫行事甚多,去春遭难,与他稿都拉杂摧烧”此句上。钱钟书《容安馆札记》本就上天入地,写到了许多我们闻所未闻,见所未见之书、之事、之人,陆灏更在其上增色添香,这就使得这篇文章密之又密,重之又重。然而让人佩服的是陆灏的文笔,举重若轻,不让人读来感觉学究与沉滞。
毛尖在评《担头看花》一书时说:“三言两语锁喉,是钱钟书黄裳辈的能力,如今传到陆公子。”初学文章的人,大概总觉得不铺排不能显露才华,有的没的写了一大堆,但其实含而不露、引而不发才是本事,更何况世故与秘辛这种东西只能点到为止。而这也形成了一种含蓄的风格。《无意中的三言两语》中陆灏写钱钟书对元曲评价很低,并批评同时代人“庸陋无识之徒乃动引莎士比亚相拟。应声之虫,吠声之狗,堪笑而亦堪哀也”。引毕此,他只淡淡说了句“这几句如果当年公开发表,不知要得罪多少人”作结。
有个读者在微博中说:“喜欢八卦的人,怎么会不看陆公子。”陆灏写的这些事,正史是上不了的,而有些事,可能当事人在其回忆文章或自传里也会自我屏蔽。然而,陆灏厉害的是,可以搜罗出与之相关的许多资料与信息,尽数罗列出来。不过,他却也不做臧否,但明眼人自是能揣测分辨。
话说回来,读陆灏《担头看花》这本书是需要相当的历史文化背景,否则不会懂得《“那么我就是众猫之王了!”》中的笑话与揶揄,不会懂得《俞平伯〈唐宋词选〉试印本》《一九四六,容庚“被迫南下”》中的苍茫历史,不会懂得《一树梅花一首诗》中童二树、袁枚二人穿越时空的相知,也不会懂得《少见而多所怪》《古风、雅贼及其他》中的幽默、自省,更不会懂得《以赛亚·伯林的初恋》中的宽容与无奈。这些文章中的历史、人情、世故、秘辛等等,用陆灏自己的话来便是:“这是假做真的故事,同则《札记》又记了真当假的故事”。
说来,陆灏的文章与董桥的文章颇为相似,翻开均是故纸味。然而,我个人还是更喜欢陆灏,董桥也忆往事,讲秘辛,然而脂粉气浓了些,陆灏则更为刚健与通透。只可惜了他“陆公子”的诨名矫情了些。
“担头看花”是个比喻,出自南宋理学家魏了翁之文,意思是很多事情没有亲自去历涉一番,就如在卖花担上看桃李,没法领会整树桃李花开的真面貌与活精神。这自然是陆灏的自谦之词了。而我等才识浅薄之人读了此书,早已觉得满目皆锦绣了。